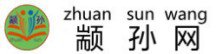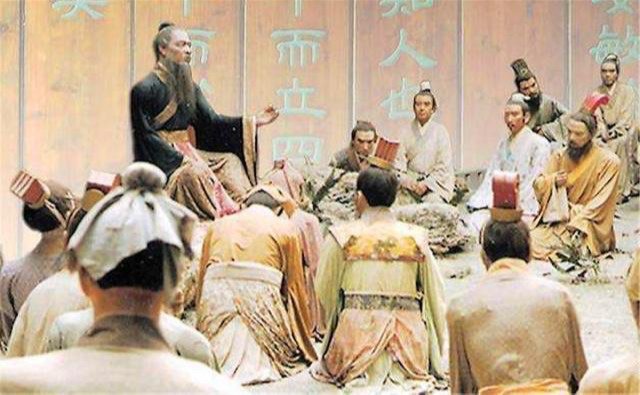|
暮春的卫国都城帝丘,护城河的水裹挟着残花向东奔流。颛孙师蹲在河岸边,指尖无意识地划着湿润的泥土,将一块棱角分明的青石磨得愈发圆润。离开家乡时,他总爱把石头攥在掌心,如今石头的边缘已被摩挲得光滑如玉,就像他自己,在孔子身边辗转两年,身上的锋芒也渐渐敛去。 “子张,仲尼先生唤你呢。” 子路的粗嗓门从身后传来,带着惯有的急躁。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十岁的师兄总是这样,说话像挥剑般直来直去。
颛孙师猛地起身,膝盖处的麻意顺着脊椎窜上后颈。他慌忙将青石塞进腰间布袋,拍了拍沾满尘土的袍角,快步朝着客栈方向走去。路过街角那棵老槐树时,瞥见子贡正倚着树干翻《诗经》,绸衫的袖口绣着精致的云纹 —— 这位卫国人总能在颠沛流离中保持体面,与自己这身浆洗得发白的麻布短褐形成鲜明对比。 “子张且慢。” 子贡合上书卷,眼角的笑意里藏着几分探究,“方才见你对着河水出神,可是在琢磨先生今早讲的‘仁者乐山’?” 颛孙师停下脚步,喉结动了动:“只是看水势湍急,想起《夏书》里‘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’的话。” 他知道自己不善言辞,每次与子贡对话都像在薄冰上行走,生怕说错什么被抓住把柄。 子贡挑了挑眉,折扇 “唰” 地展开:“卫侯最近正为黄河决堤之事烦忧,子张若有良策,何不向先生进言?” 这话像根细针,轻轻刺中了颛孙师的心事。他确实在河岸观察了三日水情,甚至画了张简易的疏水图藏在行囊里,但每次想开口,都会被更健谈的师兄们打断。去年在曹国,他曾对季孙氏的田赋制度提出异议,结果被冉有驳斥得哑口无言,那滋味至今想起仍觉喉头发紧。 “先生召唤,不敢耽搁。” 他拱手作别,转身时听见子贡在身后轻笑,那笑声里的了然让他耳根发烫。 客栈的正房里弥漫着艾草的香气,孔子坐在榻上,花白的胡须垂在深蓝色的深衣上,正对着一盏油灯批阅竹简。案几上堆着刚从卫国太学借来的典籍,其中《牧野誓》的竹简边缘已被摩挲得发亮。 “子张来了,坐。” 孔子抬眼,目光温和如春水,“方才子夏说,你昨日在市集为农夫讲解‘深耕易耨’的法子?” 颛孙师的心猛地一跳,方才在河边的从容顿时消散。他记得那农夫的草鞋沾满泥浆,指节粗大的手攥着干瘪的谷穗,眼里的焦灼像要把人烧穿。当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有人认出他是孔门弟子,便起哄让他讲讲如何能让地里多产粮食。 “只是…… 随口说说。” 他低下头,盯着自己磨出厚茧的手掌。那些话其实在心里盘桓了许久,去年在陈国看到饥荒,他便翻遍了《氾胜之书》,还向老农请教过育种的法子,只是从未在先生面前提起。 孔子放下手中的刀笔,指尖在竹简上轻轻敲击:“《周书》有云‘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’。你能将典籍里的道理用到实处,很好。” 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弟子年轻却已显坚毅的面庞,“两年前初见你时,你总爱说‘士不可以不弘毅’,如今却懂得‘讷于言而敏于行’了。” 颛孙师猛地抬头,眼眶忽然发热。他想起刚入师门时,自己总爱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,说要 “安邦定国”“致君尧舜”,被颜回私下里劝过几次,却总觉得是对方胆小怯懦。直到去年在匡地被围困,他看着先生抚琴自若,看着子路持剑护卫,才明白空谈误事的道理。 “弟子…… 还差得远。” 他声音发涩,腰间的青石硌得皮肉生疼。 “十九岁能有这份进益,已是难得。” 孔子拿起案上的《周易》,翻到 “乾卦” 那页,“明日随我去见蘧伯玉,这位卫国大夫最懂‘慎独’之道,你多听听他说话。” 走出正房时,月光已爬上客栈的飞檐。颛孙师靠在廊柱上,摸出腰间的青石。石头被体温焐得温热,就像先生方才的话语。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离家那日,父亲将这石头塞进他手里:“石虽顽,久磨成玉。做人也一样,别总想着崭露头角。” 当时只当是老生常谈,此刻才品出其中滋味。 “子张师兄。”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,是刚入门半年的公孙龙。少年捧着一摞竹简,灯笼的光晕在他脸上跳动,“方才听子游师兄说,先生夸你稳重了?” 颛孙师点点头,忽然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。他想起自己年少时,多么渴望得到前辈的认可。“公孙,” 他斟酌着词句,“你看这月光,” 他指向庭院里的桂树,“满月时固然明亮,可弦月也有它的清辉。做学问就像月亮阴晴,不必急着圆满。” 公孙龙眼睛一亮,抱着竹简的手臂紧了紧:“弟子明白了!就像师兄你,以前总爱和我们辩论,现在却……” 少年忽然住口,脸涨得通红,“弟子失言!” 颛孙师却笑了,他想起去年在宋国,自己因为和子夏争论 “礼之本” 面红耳赤,气得三天没说话。如今想来,那时的固执多么可笑。“没什么,” 他拍了拍公孙龙的肩膀,“你说得对,人总是要变的。” 夜风带来远处的梆子声,已是三更天。颛孙师回到自己与冉雍同住的偏房,借着月光看见冉雍还在抄写《春秋》。这位师兄出身微贱,却比谁都刻苦,案几上的油灯用得只剩小半盏,仍不肯歇息。 “回来了?” 冉雍抬头,笔尖在竹简上留下最后一笔,“方才子贡和子游在隔壁议论,说你这半年像换了个人。” 颛孙师解下腰间的布袋,将青石放在枕边:“他们又说我什么了?” “说你以前见了达官显贵就往前凑,如今卫侯派人来请,你反倒躲在后面看书。” 冉雍放下笔,揉了揉酸胀的手腕,“还说你现在解经,能把《尚书》里的话和田间地头的事结合起来,比子夏讲得还透彻。” 颛孙师的脸微微发烫。他记得上个月卫国大夫孔圉来访,自己确实在偏房读《酒诰》,因为正好读到 “祀兹酒” 那句,想起昨日看到市集上有人酗酒闹事,便忍不住多琢磨了几句。 “不过是碰巧罢了。” 他躺下时,青石硌在颈下,倒也舒服。 冉雍吹熄油灯:“子张,你可知为何先生总说‘三人行必有我师’?” 黑暗中传来布料摩擦的窸窣声,“不是要我们学别人的长处,是要我们看见自己的短处。你这半年,最难得的就是这点。”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颛孙师攥着那块青石,想起今早路过学堂,听见几个孩童在读《诗经》,其中有个扎总角的小姑娘把 “如切如磋” 念成了 “如切如搓”,旁边的教书先生却笑着说:“没错,玉石要搓,学问也要磨。”
他忽然明白,自己这块顽石,正在被岁月、被师友、被这颠沛流离的旅程,一点点磨去棱角。而那些曾经觉得刺耳的批评、难堪的沉默、挫败的瞬间,都像磨石上的砂砾,让他渐渐显露出温润的质地。 天快亮时,颛孙师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回到陈州的老宅,父亲正在院子里凿一块青石,火星溅在他的粗布衣裳上。“这块石头,要雕成镇纸。” 父亲说,“不能太尖,也不能太滑,要让人握着舒服,压得住纸,又不伤人。” 醒来时,东方已泛起鱼肚白。他摸出枕边的青石,对着晨光端详。石头的侧面有道浅浅的刻痕,是他十七岁那年用刀笔刻下的 “勇” 字,如今已被磨得几乎看不见。他忽然想,或许真正的勇敢,不是锋芒毕露,而是懂得收敛光芒,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 客栈外传来马车轱辘声,该随先生去见蘧伯玉了。颛孙师将青石仔细收好,起身整理衣袍。铜镜里映出一张年轻的脸,眉宇间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,却已少了几分躁动,多了几分沉静。 他推开房门,看见子贡正站在院里喂马,绸衫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。“子张,蘧大夫家的门客都爱讨论《周易》,你昨晚看的那卷《系辞》,正好能派上用场。” 子贡递过来一个油纸包,“这是刚买的胡饼,路上吃。” 颛孙师接过温热的胡饼,指尖触到对方微凉的指腹,忽然想起两年前在郑国,自己因为抢了子贡的座位而争执不休。“多谢子贡师兄。” 他低头咬了一口胡饼,芝麻的香气在舌尖弥漫开来。 “走吧,先生在马车里等了。” 子贡转身时,嘴角扬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。 马车碾过青石板路,发出规律的声响。孔子闭目养神,手指在膝上轻轻打着节拍。颛孙师翻开《周易》,阳光透过车帘的缝隙落在 “谦卦” 上,那些古老的文字仿佛活了过来,在竹简上跳跃、流淌。 他忽然想起冉雍昨晚的话,想起子贡递来胡饼时的温度,想起先生温和的目光,想起那个念错诗句的小姑娘。原来成长从来不是孤孤单单的打磨,而是无数双手、无数双眼、无数颗心,在不经意间,将你雕琢成更好的模样。 马车驶过护城河时,颛孙师撩开车帘,看见昨日那个农夫正在河边修整农具,晨光洒在他黝黑的脸上,泛着健康的光泽。他忽然觉得,自己这块被岁月打磨的石头,或许有一天,也能像河边的青石一样,沉默地铺就一条路,让后来者走得更稳、更远。 蘧伯玉的府邸藏在巷陌深处,朱漆大门上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。门吏引着他们穿过天井,看见满园的兰草正在晨露中舒展叶片。这位年近七旬的卫国大夫穿着粗布便袍,正蹲在花圃里拔除杂草,动作迟缓却沉稳。 “孔丘兄大驾光临,有失远迎。” 蘧伯玉直起身,掸了掸衣襟上的泥土,目光落在颛孙师身上时微微一顿,“这位便是你常说的颛孙师吧?” 孔子笑着点头:“正是犬徒,蒙蘧兄挂念。” 颛孙师躬身行礼,听见蘧伯玉对孔子说:“前日听孔圉说,令徒在市集讲解‘富民’之道,言辞虽朴,道理却深。” 他的脸又开始发烫,正想谦虚几句,却被孔子打断:“子张,蘧大夫研究《周易》六十余载,你前日不是对‘时乘六龙’有疑问吗?正好请教。” 颛孙师定了定神,从行囊里取出自己批注的竹简:“弟子以为,‘六龙’并非实指,而是喻指君子处世当如龙之变化,或潜或跃,皆应其时……” 他越说越流畅,那些在心里盘桓多日的想法,此刻像泉水般汩汩涌出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