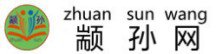|
鲁哀公十年的初夏,卫国都城帝丘的空气里弥漫着槐花与尘土混合的气息。颛孙师背着半旧的书箧,紧跟在孔子身后穿过熙攘的市集,青铜编钟的余韵从宫城方向断断续续飘来,像极了曲阜老家祠堂里的晨钟。市集上吆喝声此起彼伏,卖布的商贩正拿着一匹素色麻布向妇人推销,街角的孩童追逐着一只衔着麦穗的麻雀,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 “子张,你看那卖豚肉的老丈。” 孔子忽然驻足,花白的胡须在风里微微颤动,“他称肉时总多添半指,三年前我等初至帝丘便见过,如今仍是这般。”
颛孙师顺着先生的目光望去,那屠夫正用粗粝的手掌拍着案板,竹制的衡器在阳光下泛着油光。案板上的豚肉色泽鲜亮,肥瘦相间,不时有苍蝇嗡嗡地飞来,又被屠夫挥手赶走。他刚要答话,街角突然冲来个身着粗麻短打的少年,怀里揣着的竹简硌得衣料鼓鼓囊囊,见到孔子便直挺挺跪倒在地,膝盖与青石板碰撞的声响在喧闹的市集里格外清晰。 “夫子!曲阜来的急信!” 少年的声音带着哭腔,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,顺着脸颊滑落,滴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水渍。 孔子接过竹简的手指突然收紧,颛孙师看见先生指节泛起的青白。竹简上的墨字被汗水洇开了边角,冉求那笔力遒劲的字迹此刻却显得格外刺眼 ——“夫人体中不适,弟子侍侧,汤药未辍”。短短十几个字,却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,在众人心中激起千层浪。 “何时得的信?” 孔子的声音比寻常低沉许多,像是从枯井深处传来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 “三日前曲阜南门发的快马,小的换了五匹坐骑才赶在今日送到。” 少年抹着额头的汗,气息还未平复,“冉求师兄说,夫人生病已有月余,只是怕扰了夫子周游,一直没敢报……” 颛孙师注意到孔子背后的手紧紧攥着,指缝间渗出些微血丝。同行的子贡慌忙扶过先生,他的手也有些发抖,小心翼翼地支撑着孔子的身体,生怕先生会支撑不住。颜回已转身去寻客栈,他的脚步匆匆,背影在人群中穿梭,很快便消失在街角。子路则按着腰间的剑站在路口,眉头紧锁,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周围,像是要挡住所有可能带来坏消息的风。 那夜的卫国客栈,烛火在窗纸上投下孔子枯坐的影子,忽明忽暗。客栈里很安静,只能听到窗外偶尔传来的虫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颛孙师躺在隔壁的草席上,辗转难眠,听着先生反复摩挲那卷竹简的沙沙声,每一声都像敲在他的心上。直到天快亮时,才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:“伯鱼若是还在,也该替我尽孝了。” 那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思念与遗憾,让颛孙师的心也跟着揪紧了。 七日后的清晨,天色刚蒙蒙亮,东方泛起一丝鱼肚白。第二个信使撞开客栈门时,颛孙师正帮先生整理衣冠。先生今日要去卫国太庙,他特意换上了一件整洁的深衣,颛孙师正仔细地为他系好衣带。那人手里的竹简用麻绳捆着,墨迹透过竹片渗到外面,颛孙师一眼就瞥见了 “病情骤重” 四个字,指尖突然发起抖来,系衣带的手也停住了。 孔子展开竹简的手在颤抖,烛台被带倒在地,“哐当” 一声,蜡油溅在他的深衣下摆上,凝固成一块块黄色的印记。“亓官氏……” 他喃喃念着夫人的名字,这个从少年时便陪伴他的女子,这个在他周游列国时独自支撑家宅的女子,此刻正隔着千里生死线,向他发出最后的召唤。他的眼神空洞,仿佛灵魂已经飘向了远方的曲阜。 “备车!回曲阜!” 子路的吼声震得房梁落灰,他急得满脸通红,手紧紧握着剑柄,指节都泛白了。但孔子却摇了摇头,他的目光缓缓移向窗外,望着卫国的天空,那里飘着和曲阜一样的流云,只是此刻在他眼中,这流云也带着一丝忧伤。“定公新丧,哀公正幼,鲁国政局未稳。我等若此时离去,卫君托付的礼制修订之事如何交代?” “可夫人她……” 子贡急得满脸通红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却被孔子抬手止住。先生转身走向案几,提笔在竹简上写下 “敬候消息” 四字,笔锋却在 “候” 字的竖钩处断了墨,墨汁在竹简上晕开一小团,像是一个未完成的句号。 接下来的日子,孔子依旧按时去卫国太庙商议礼法,只是脚步慢了许多,背影也显得愈发佝偻。太庙庄严肃穆,梁柱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,空气中弥漫着檀香的味道。有次讲解《仪礼》中昏礼一节,说到 “亲迎于户” 时,他突然停住,目光透过太庙的窗棂望向东南方,那里是曲阜的方向。阳光从窗棂照进来,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颛孙师看见先生喉结滚动,许久才低声道:“当年我迎娶亓官氏,也是这般亲自迎到门口。那时她穿着一身红衣,站在门口,笑起来眼睛像弯弯的月牙。” 颜回每日去驿站打听消息,他总是早早地出发,傍晚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影回来,带回的总是 “尚无音讯”。每次听到这四个字,他都会露出失望的神情,然后默默地走到一旁,低头不语。子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磨佩剑,剑穗上的红绸被他攥得褪了色。他打磨得格外认真,剑身被磨得光亮如镜,能映出他坚毅的脸庞,仿佛这样就能驱散心中的焦虑。子贡悄悄备好了马车,缰绳就系在客栈的廊柱上,马车上还放着一些干粮和水,随时等着先生一声令下,便能立刻出发。 鲁哀公十年六月壬申,卫国刚下过一场暴雨,天空阴沉得可怕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,汇成水流顺着房檐流下,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小水洼。信使第三次到来时,浑身淌着泥水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,手里的竹简用油纸裹着,却还是湿透了大半。他跪在孔子面前,将竹简举过头顶,身体因为寒冷和紧张而不停颤抖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:“夫子…… 夫人…… 薨了。” 颛孙师觉得整个客栈都在摇晃,耳边嗡嗡作响,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声音。孔子接过那卷沉甸甸的竹简,手指触到油纸下冰冷的竹片,像是摸到了亓官氏早已冰凉的手。竹简上冉求的字迹潦草仓促,“戊寅日丑时,夫人溘然长逝,弟子们已按礼制入殓”,最后还有一行小字:“夫人临终前问,夫子何时归。” 那一行小字,像一把锋利的刀,刺穿了孔子的心。 孔子站在原地,雨水从信使的蓑衣上滴落在地,汇成小小的水洼。他没有哭,只是把竹简紧紧贴在胸口,仿佛这样就能离千里之外的亡妻近一些。过了很久很久,久到颛孙师以为时间都静止了,他才抬起头,望着雨幕中的帝丘城,城墙在雨中显得模糊不清,声音平静得让人心惊:“知道了。” 那天下午,孔子依旧去了太庙。卫君见他面色憔悴,眼窝深陷,眼下有着浓重的黑青,劝他回去休息。他却躬身行了大礼,动作标准而恭敬:“臣闻,礼者,事人如事天。亓官氏一生守礼,必不愿见我因私废公。” 他讲解《丧服》篇时,每个字都清晰沉稳,只是讲到 “夫为妻服齐衰杖期” 时,手中的木简突然掉在地上,发出 “啪” 的一声,在寂静的太庙中格外响亮。 黄昏回到客栈,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,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孔子解下冠缨,坐在案前开始削制丧杖。桃木在他手中渐渐成形,削下的木屑积在脚边,像一堆细碎的雪。颛孙师想上前帮忙,却被颜回拉住。颜回摇了摇头,示意他退下,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 —— 此刻的先生,正用自己的方式与亡妻告别,旁人不宜打扰。 深夜,万籁俱寂,只有烛火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。颛孙师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,那哭声低沉而悲伤,像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的。他悄悄走到先生门外,透过门缝往里看,看见烛火下孔子正对着一件旧襦裙垂泪。那是亓官氏年轻时亲手缝制的,领口处还绣着小小的兰草,针脚细密,边角已经磨得发白。先生用手指轻轻抚摸着针脚,泪水滴在布面上,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 “当年我在季氏家做委吏,俸禄微薄,你总把好的布料给我做深衣,自己却穿这旧襦裙。” 孔子的声音哽咽着,像个迷路的孩童,“我说要周游列国,你连夜给弟子们缝补行装,灯下的线轴转啊转,转得我心里发酸…… 还记得有一次,我深夜归来,你还在灯下为我缝补袜子,手上被针扎了好几个小孔,却笑着说不碍事。” 颛孙师捂住嘴,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,泪水却像断了线的珠子,无声地滑落。他想起初入孔门时,曾在曲阜见过亓官氏。那时她已两鬓斑白,脸上布满了皱纹,却总是笑眯眯地给晚来的弟子留着饭食。冬天会把炭火往贫寒弟子身边推,让他们能暖和一些;春天则采来院里的桃花插在书案上,给清冷的屋子增添一抹亮色。 出殡前七日,孔子带领弟子们在卫国客栈设了简易的灵堂。没有棺椁,没有牌位,只有亓官氏那件旧襦裙挂在墙上,前面摆着三牲祭品,有刚宰杀的猪、羊,还有新鲜的鱼,散发着淡淡的腥味。孔子每日清晨都要对着襦裙行稽首大礼,动作缓慢而庄重,然后继续去太庙工作,傍晚回来便坐在灵前,一动不动,直到烛火燃尽,房间陷入一片黑暗。 有次子路忍不住问:“夫子,为何不回去送夫人最后一程?” 他的声音带着不解和一丝怨气,觉得夫子太过于固执。 孔子望着墙上的襦裙,良久才道:“君子不以私害公。亓官氏知我,必懂我。” 但颛孙师看见,先生转身时,袖角沾着的烛泪正在往下滴,在地面上留下一小片湿润的痕迹。 颜回开始整理孔子近年来的言论,准备编纂成书。他坐在案前,一笔一划地抄写着,神情专注而虔诚,仿佛这样就能为先生分担一些痛苦。子贡则派人快马加鞭送去丧礼所需的帛币,叮嘱冉求务必按最高规格安葬,不能委屈了师母。子路把佩剑挂在灵堂旁,剑柄擦拭得锃亮,说要替夫子守护着夫人的灵位,不让任何邪祟侵犯。
颛孙师每日都在灵前添灯油。他发现那盏油灯的灯芯总是被人修剪得很短,火焰小小的,昏昏暗暗的。想来是先生夜里独坐时,怕灯火太亮惊扰了亡妻。有次他深夜添油,看见孔子正对着襦裙轻声诵读《诗经》:“葛生蒙楚,蔹蔓于野。予美亡此,谁与独处?” 那声音低沉而忧伤,在寂静的夜里回荡,让人听了心碎。 鲁哀公十年七月庚辰,曲阜传来消息,亓官氏已葬于防山。孔子听到消息时,正在太庙核对一份礼器清单。清单上的礼器名称密密麻麻,他却看得格外认真。他放下手中的木简,向着东南方躬身行礼,动作缓慢而郑重,仿佛在与亡妻做最后的告别。起身时,众人发现他的鬓角又白了许多,像是落了一层霜,更显苍老。 回到客栈,孔子取下墙上的襦裙,小心翼翼地仔细叠好放进木匣,每一个动作都轻柔无比,像是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。他对弟子们说:“明日起,恢复讲学。” 那日的讲学设在客栈的庭院里,院子里的槐树郁郁葱葱,枝叶繁茂。孔子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,弟子们围坐在他周围。他讲的却是《孝经》,声音平和而沉稳。阳光透过叶隙落在他身上,忽明忽暗,为他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。讲到 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 时,他突然停住,望着远方的天空说:“亓官氏嫁我三十余年,替我奉养父母,教养子女,我却未能在她临终前守在身边。她总是为我着想,从未抱怨过一句,这份恩情,我无以为报啊。”
颛孙师看见先生的眼眶红了,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,顺着脸颊流下,滴在衣襟上。这是亓官氏去世后,他第一次落泪。泪水落在泥土里,很快洇了进去,像要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,为那个素未谋面的师母留下一点痕迹。 弟子们都低着头,谁也没有说话。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息,风吹过槐树,叶子沙沙作响,像是亓官氏在遥远的曲阜回应着先生的思念,温柔而绵长。 三个月后,孔子完成了卫国的礼制修订工作。那些日子里,他白天与卫国的大臣们商议修订的细节,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,夜晚则在灯下仔细核对,常常忙到深夜。离开帝丘那天,天刚蒙蒙亮,东方的天空泛起一抹淡淡的红霞。子贡备好的马车早已等候在门口,马夫牵着马,静静地站在一旁。孔子上车前,突然转身对着东南方深深一拜,弯腰时,花白的胡须几乎触到了地面。颛孙师扶着先生的胳膊,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,那颤抖里有愧疚,有思念,还有一种穿越生死的相守。 马车驶离帝丘时,颛孙师回头望去,看见朝阳正从城墙上升起,金色的光芒洒满了大地,照亮了客栈的窗棂。他想起那些日子里,先生枯坐的身影,颤抖的双手,无声的泪水,还有那件挂在墙上的旧襦裙。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他忽然明白,夫子之所以为夫子,不仅在于他坚守的礼制与道义,更在于他将常人的喜怒哀乐,都化作了践行大道的力量。而亓官氏,这位从未出现在《论语》中的女子,却以她的一生,为孔子的道,铺就了最温暖的底色。她的付出与理解,是孔子能够安心周游列国、传播思想的坚强后盾。 马车一路向东,车轮碾过尘土,发出沉稳的声响,像是在诵读一首无声的诗,写给千里之外的亡妻,也写给这颠沛流离却从未停歇的道。道路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向后退去,仿佛在诉说着这段旅程的漫长与艰辛,也见证着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执着与坚守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