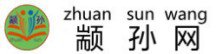|
鲁哀公七年的深秋,卫国都城帝丘的护城河结着薄冰,寒鸦在颓圮的城堞上聒噪。孔子的马车碾过结霜的土路,车轴发出吱呀的呻吟。颛孙师掀起车帘一角,望着远处巍峨的宫殿群,朱红的宫墙在暮色中泛着冷光,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匍匐在大地上。 “子贡,” 孔子的声音从车帷深处传来,带着旅途的疲惫却依旧沉稳,“你看这帝丘城,与十四年前咱们初来时,有何不同?”
颛孙师听到孔子询问师兄,子贡回答:“夫子,城墙更矮了,西郭的工坊区却扩了三倍不止。当年守城门的老兵总念叨‘卫多君子’,方才我见城门吏盘查商贾时,眼里尽是铜锈色。” 孔子轻轻叩击着车厢壁上的竹简:“卫灵公当年问阵于我,如今继位的出公,怕是连先君的弓都拉不开了。” 话音未落,车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颛孙师警觉地握紧腰间的佩剑。 三名披甲骑士勒马挡在车前,为首者头盔上的红缨沾满尘土:“来者可是孔丘?” 颛孙师正要回话,孔子却已掀帘而出。七十岁的老者立在寒风中,宽大的儒袍被风掀起,宛如一面不屈的旗帜。 “吾乃孔丘。” 简单的三个字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骑士们交换了个眼神,忽然翻身下马:“君上有请。” 穿过七道城门时,颛孙师注意到墙缝里钻出的枸杞藤,叶片上还挂着昨夜的霜花。宫殿的铜环门被推开的瞬间,一股混杂着香料与酒气的暖流传了出来。卫出公坐在堂上,腰间的玉璧随着他不安分的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。 “孔夫子远道而来,” 年轻的君主努力挤出笑容,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,“寡人听闻夫子在陈蔡之间……” “困于野,七日不火食。” 孔子接过话头,语气平静无波。他转向身后的弟子们,“子贡用五乘之礼说动楚君,子路在林间射得三鹿,而子张 ——” 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颛孙师身上,“在断粮第三日,仍坚持每日温习《诗》三百。” 颛孙师耳根微热,想起那个艰难的日子。卫出公拍了拍案几上的青铜甗,转移了话题:“夫子此番回来,可有安邦良策?” 孔子走到堂中,望着梁柱上斑驳的漆画:“臣以为,为政先须正名。” “正名?” 卫出公嗤笑一声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的竹简,“去年我派使者去鲁国,要回了先君的宝鼎,这算不算正名?” 颛孙师上前一步,腰间的佩剑轻响:“君上,鼎之轻重,在德不在力。当年夏桀失德,鼎迁于商;商纣失德,鼎迁于周。如今君上虽得宝鼎,却让大夫弥子瑕专权,百姓都说‘其子之裘,其父之政’——” “放肆!” 卫出公猛地站起,腰间的玉璧相撞发出刺耳的声响,“你是什么人?” “鲁国颛孙师,字子张。” 他挺直脊梁,目光如炬,“臣在陈地时,曾见农夫移苗,若根茎不正,施肥再多亦是徒劳。” 孔子微微颔首: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粟,吾得而食诸?” 卫出公的脸色由红转白,他踉跄着坐回席上,手指颤抖地端起酒爵,却洒了半杯在衣襟上。“夫子是说……” “君要像君,臣要像臣。” 孔子缓步走到窗前,望着庭院中那棵歪斜的老槐树,“就像这树,若主干弯曲,旁枝再繁茂也是枉然。” 当晚,孔子师徒被安置在公孙朝的府邸。颛孙师在灯下整理竹简,忽然听到院墙外传来争执声。他悄悄爬上柴房的草垛,借着月光看到两个身影在桂树下对峙 —— 卫出公的太傅孔文子和大夫弥子瑕。 “孔子想废了公子蒯聩的世子位?” 弥子瑕的声音尖利如枭。 孔文子的声音压得很低:“君上怕的是流亡在外的父亲回来夺位。” 颛孙师猛地捂住嘴,差点惊出声来。他想起白天孔子说的 “父不父,子不子”,原来夫子早已看透了这层隐情。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,颛孙师便起身来到庭院。此时,子路正借着晨光擦拭他的佩剑,那剑刃在微光中闪着凛冽的寒光。子贡则坐在一旁的石凳上,手里捧着一卷竹简,神情专注。 “子张,你来得正好。” 子路看到他,停下手中的动作,“昨日在朝堂上,你那般直言,怕是让卫出公心生不满了。” 颛孙师走到子路身边,也拔出自己的剑,轻轻拂过剑身:“子路兄,夫子教导我们要‘当仁不让’,面对君上的不当之举,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吗?” 子贡放下竹简,摇了摇头:“子张,并非不让你直言,只是言辞需有分寸。卫出公本就对夫子心存疑虑,你那般直接,怕是会让他误会夫子有意干涉卫国朝政。” “可‘正名’之道,本就该直指要害。” 颛孙师有些不服气,“若君不君,臣不臣,国将不国。我们追随夫子周游列国,不就是为了宣扬这些道理吗?” 子路叹了口气:“话虽如此,但世事复杂。卫出公与他父亲蒯聩的矛盾由来已久,岂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?你那般说,无疑是捅了马蜂窝。” 颛孙师还想争辩,却见颜回从屋内走出。颜回向来沉静,此刻却面带忧色:“诸位师弟,方才我听闻,卫出公的内侍在府外徘徊许久,似乎有要事。” 众人闻言,皆是一怔。子贡沉吟道:“怕是与昨日朝堂之事有关。”
果然,没过多久,卫出公的内侍便捧着锦盒走了进来,脸上堆着谄媚的笑:“子张先生,君上赏的。” 颛孙师打开锦盒,里面竟是一副象牙剑鞘,雕工精美。他正疑惑间,内侍压低声音:“君上想问,若要正名,是否该先除掉流亡在晋的蒯聩?” 颛孙师猛地合上锦盒,声音冷得像结了冰:“你回去告诉君上,夫子说过,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。” 内侍灰溜溜地走后,子贡摇着扇子:“子张这脾气,早晚要吃亏。” 颛孙师收剑入鞘:“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君上做悖逆之事?” “夫子昨晚修订《春秋》,特意在‘卫侯辄出奔’那句话旁画了三个圈。” 子贡凑近一步,“你说,夫子是在提醒谁?” 颛孙师沉默了,他知道子贡说得有道理,可心中的那份执念却让他无法认同这种迂回的方式。 这时,颜回开口了:“子张,夫子的‘正名’,并非只靠言辞说教。就像这天地运行,自有其规律,强行干预只会适得其反。我们能做的,是以身作则,让世人看到‘礼’的真谛。” 颛孙师看着颜回,忽然想起昨日在朝堂上夫子的眼神,那眼神中既有赞许,也有一丝担忧。或许,自己真的有些操之过急了。 正说着,孔子的声音从月亮门边传来:“今日要去南郭的蘧伯玉家,你们谁愿同往?” 颛孙师第一个应声:“弟子愿往!” 路上,师徒几人沿着街道缓缓前行。街道两旁,商贩们已经开始张罗生意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 “夫子,” 颛孙师忍不住问道,“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,他对‘正名’之道可有独到的见解?” 孔子捋了捋胡须:“蘧伯玉一生致力于‘仁’的实践,他对‘正名’的理解,或许更侧重于自身的修养。” 子路接口道:“自身修养固然重要,但若不能影响君主,那又有何用?” “子路,” 孔子看了他一眼,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修身是根基。若自身不正,何以正人?” 子贡点头附和:“夫子所言极是。就像这街道上的商贩,若个个都能诚信经营,不欺瞒顾客,那整个市场自然就井然有序。这便是‘正名’在小处的体现。” 颛孙师听着众人的话,心中渐渐明朗。原来 “正名” 并非只是对君主的要求,更是对每个人的期许。 蘧伯玉的府邸朴素无华,院墙爬满了牵牛花。八十岁的老者拄着竹杖,见到孔子便倒身便拜:“夫子回来,卫国有救了!” 孔子扶起他:“蘧老大夫说笑了,我不过是个周游列国的匹夫。” 两人在堂上论道时,颛孙师在院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—— 正是昨天挡路的骑士头目。那人见到他,慌忙躲进了柴房。颛孙师心中起疑,悄悄跟了过去。 柴房里堆满了竹简,骑士正往麻袋里装东西,听到脚步声,猛地回头,腰间的匕首闪着寒光。“你想干什么?” “这些是蘧家的典籍?” 颛孙师注意到竹简上的印章。 骑士忽然跪地:“子张先生救命!弥大夫逼我偷蘧老的书信,说里面有通敌的证据。我若不做,妻儿就要被卖去为奴!” 颛孙师这才注意到他甲胄下露出的伤痕,新旧交错。“起来吧,” 他扶起骑士,“这事我替你担了。” 回到堂上时,孔子与蘧伯玉正谈论着音律。颛孙师在一旁静静聆听,心中却在思索如何化解这场危机。 过了一会儿,子路悄悄凑到颛孙师身边:“子张,你刚才去柴房看到了什么?那骑士鬼鬼祟祟的,怕是没什么好事。” 颛孙师把刚才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子路。子路听完,怒目圆睁:“弥子瑕太过放肆,竟敢如此陷害贤良!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。” “子路兄稍安勿躁,” 颛孙师拉住他,“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,若是贸然行事,反而会打草惊蛇。” 子贡也走了过来:“子张说得对。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,既能揭穿弥子瑕的阴谋,又能保护蘧老大夫和那骑士。” 三人在一旁低声商议着,孔子和蘧伯玉似乎察觉到了他们的异样。 “你们在商议什么?” 孔子问道。 颛孙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孔子。孔子沉思片刻:“弥子瑕此举,不仅是针对蘧伯玉,更是想借机打压我们。我们必须谨慎应对。” 蘧伯玉叹了口气:“弥子瑕专权已久,朝中敢反对他的人寥寥无几。若不是夫子到来,我恐怕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。” “老大夫放心,” 孔子坚定地说,“邪不胜正,我们定能让他的阴谋落空。” 正说着,外面传来喧哗声。弥子瑕带着甲士闯了进来,指着孔子:“奉君上令,捉拿通敌叛国的蘧伯玉!” 蘧伯玉从容不迫:“弥大夫可有证据?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