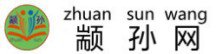|
朱子《论语集注》曰:“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,故常过中。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,故常不及。”正可见出二人之为人处世及性格气质之鲜明对比。这不仅可以《子张》中论交友一章可证,尚可以《礼记·檀弓上》所记佐证:“子夏既除丧而见,予之琴,和之而不和,弹之而不成声。作而曰:‘哀未忘也,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。’子张既除丧而见,予之琴,和之而和,弹之而成声。作而曰:‘先王制礼,不敢不至焉。’”正是一过一不及之证。 另外在《韩诗外传》卷九记有子张与子夏之辩论,“二子相与论,终日不决”,可见其二人观点之差异,性格气质之不同。“子夏辞气甚隘,颜色甚变”,而子张则讥讽其为“小人之论”,而子张则主张议论时应当“徐言闇闇,威仪翼翼,后言先默,得之推让,巍巍乎,荡荡乎”,这与子张重威仪容止有关,当然也可见二者气质之差异。 那么,是否据此可以得出二人关系甚恶之结论呢?我看未必。从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”一例可知,二人虽然性格气质与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,但二人未必会交恶。当然,我们也不一定以为二人关系会非常融洽。品味起来,子夏与子张、子游的关系,不如子张与子游、曾子的关系融洽,亦不如子夏与曾子之关系亲密。 子夏与子张之思想分歧,正是基于其性格气质之差异。观子夏所言:“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”,乃发挥夫子“无友不如己者”之意,而子张“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”的主张,也同样是接闻于夫子,因气质之差异而各得夫子之一偏。子夏气象狭促但守于谨慎,子张气象阔大但偏于疏狂。从下文子夏与子游之互相批评亦可见,子夏重学,重小道,子游则重大道,气象与子张相仿佛。由此看来,子夏与子张、子游之关系皆不甚慕。 子游评价子张之语,一般皆以为是有褒有贬,以贬为主。如皇侃《义疏》引袁氏云:“子张容貌难及,但未能体仁也。”朱子注曰:“子张行过高,而少诚实恻怛之意。”而清儒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则认为:“孔子论仁多以其易者言之,……惟过故为难能,惟难能故未仁。子游此论极合孔子论仁之旨,非先以容仪难及美之,而后以未仁讥之也。”康有为《论语注》则认为:“孔子没后,同门中子张年少而才行最高,……记《论语》者为曾子之徒,与子张宗旨大异,乃误传其有所短也。”程树德亦不同意子游讥之之说。他引王闿运《论语训》“非贬子张未仁也,言己徒希其难,未及于仁”之说,指出,“此‘友’字系动词,言我所以交子张之故,因其才难能可贵,己虽有其才,然未及其仁也。……未仁指子游说,如此既可杜贬抑圣门之口,且考《大戴礼·卫将军文子篇》孔子言子张‘不弊百姓’,以其仁为大。是子张之仁固有确据。”综合考量王、程之说,别出心裁,与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、《大戴礼记·文将军文子》所载相符,确可从。 曾子评价子张之语,何晏《集解》引郑曰:“言子张容仪盛,而于仁道薄也。”皇侃、邢昺、朱子皆同此说。康有为《论语注》云:“类叙攻子张之意。……曾子守约,与子张相反,故不满之。人之性,金刚水柔,宽严异尚,嗜甘忌辛,趣向殊科,宗旨不同则相攻。……孔子许子张,几比于颜子,可谓定论。论人当折衷于孔子。记《论语》者当为曾子后学,而非子张之徒,故记本师之言,……未可为据。”然而,皇侃《义疏》引江熙曰:“堂堂,德宇广也。仁,行之极也。难于并仁,荫人上也。”继而指出:“江熙之意,是子张仁胜于人,故难与并也。”清儒戴望《戴氏注》:“言子张行高为仁,人难与并,叹其不可及。”王闿运《论语训》云:“亦言子张仁不可及也。难与并,不能比也。曾、张友善如兄弟,非贬其堂堂也。”程树德认同王说,并言:“如旧注之说,子游、曾子皆以子张为未仁,摈不与友,《鲁论》又何必记之?吾人断不应以后世讲朱陆异同之心理推测古人。况曾子一生最为谨慎,有口不谈人过之风,故知从前解释皆误也。王氏此论虽创解,实确解也。” 程说所指亦应包括康氏在内。黄怀信先生虽然坚持子游之语乃贬语,但他认为此处曾子之语与子游不同,难与,不可及也,并,共同、一起。因此他同意王闿运之说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