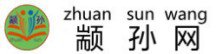|
其三:《檀弓上》:“子张病,召申祥而语之曰:‘君子曰终,小人曰死;吾今日其庶几乎?’”而申祥,后为鲁穆公之臣,由这一个角度看,其后代在鲁出仕,尽管不能排除其居陈且卒于陈(楚),但相较而言,其为鲁人之可能性较大。 综上而言,子张可能曾于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离鲁适陈(楚),后又返鲁,最后卒于鲁。 子张氏颛孙,而据《风俗通》:“陈公子颛孙仕鲁,因颛孙为氏。”《世本·氏姓篇》(秦本):“颛孙氏,陈公子颛孙仕鲁,因氏焉。其孙颛孙师字子张,为孔子弟子。”考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:“二十二年春,陈人杀其大子御寇,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。颛孙自齐来奔。”据此,则此陈公子颛孙即子张之先祖。《左传》云“来奔”即奔鲁。而据《世本》、《风俗通》,其人继而仕于鲁。而颛孙再不见于传文,应该是在鲁繁衍,并未归陈。自庄公二十二年(前672年)至子张生时(前503年),已历百七十年,至少已有五六世之传衍。《吕氏春秋》云“鲁之鄙家”,可知其家已衰败,非贵族矣。至于《尸子》所云“颛孙师驵也”,驵,为马贩子,则不知是否属实了,姑且存疑。 其实,陈人说与鲁人说并不矛盾。因为子张先祖为陈人,依孔子先祖为宋人而自称宋人或殷人之例,云子张为陈人自无不可。而子张则生于鲁国,既长从孔子游,孔子卒后,子张居陈,开宗立派,自成一家,而陈旋又为楚所灭,子张之儒在楚地当有相当之影响,这一点可从楚地出土简帛文献得以印证。 二、子张应属于“政事派” 子张在孔门之中属于性格较为鲜明者,这种性格与气质直接影响到他对孔子思想的接受程度与学问境界,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思想特征。而这种性格气质和思想特征,也使其在孔门当中别具特色,可以形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派。郭沫若将子张定为“过激派”,姜广辉称之为“表现派”,梁涛则归之为“礼容派”。胡适指出,子张因“阔大气象”,与子夏、曾子一班人不合,所以别立宗派。梁启超亦同此论,指出子张在孔门“最为阔大”,郭沫若称其“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”,并由此提出与墨子一派的因缘关系。那么这些说法,到底是否准确、妥帖?子张为何能别立宗派,原因何在?这就牵涉到子张之性格气质与思想特色了。 今人在研究子张之“别立宗派”时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据,便是据《论语》中子张与同门的关系不融洽。上引胡适之说如此,郭沫若亦有此意。今人吴龙辉说:“据《子张》篇所载,在孔门高第中,子张是和其他弟子关系处得最差的一位。……子游说子张难能而未仁,其意思是说子张自视甚高,不把同门放在眼里。从子张对子夏论交的故意抬杠来看,子张大概是极易攻击同门的。因此,孔门其他弟子都对他心存芥蒂,不乐与之为伍。……曾参在孔门中以善能动心忍性、乃至愚忠愚孝著称。他都对子张不能忍受,则其他弟子就更为可知了。既然其他同门觉得无法和子张相处(即并为仁),而子张又生性自高,那么,他就只能采取宗法制下‘别族’的方式与其他弟子分裂了。”我们通过细读《子张》的历代注疏,感到类似胡适之、吴龙辉这种看法,其来有自,然而却可能存在很大的误解。我们看《论语·子张》篇所载子张与同门关系的材料有三则。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:“子夏云何?”对曰:“子夏曰:‘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:“异乎吾所闻: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,于人何所不容?我之不贤与,人将拒我,如之何其拒人也?” 子游曰:“吾友张也,为难能也,然而未仁。” 曾子曰:“堂堂乎张也,难与并为仁。” 首先看子张与子夏的关系。二人之性格差异较大,对比甚为强烈。子贡曾经问孔子:“师与商也孰贤?”孔子评价是:“师也过,商也不及。”并进而指出:“过犹不及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从孔子中道思想的角度看,二人皆不合中道,故对二人都有批评。邢昺曰:“此章明子张、子夏才性优劣。”类似的记载见于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:“子曰:‘师!尔过而商也不及。’”在另一处,孔子评价子张说:“师也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马融曰:“子张才过人,失在邪僻文过。”王弼云:“僻,饰过差也。”皇侃云:“子张好文其过,故云僻也。”朱子曰:“辟,便辟也,谓习于容止,少诚实也。”黄式三《后案》云:“辟,……偏也,以其志过高,而流于一偏也。马注以为‘辟’为邪僻文过,固非。”对朱子之注亦不苟同。今人注此,多从黄氏之说,解释为偏激。这可能是对的。那么,有孔子所谓“师也辟”,是否可以将之称为“过激派”,我们认为也不妥当。“过激派”容易予人以子张行事与思想偏激之印象,而这种印象往往会引向消极或否定的认识。这不利于正确估量子张之儒的价值。而且类似的命名和归类,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如果照此划分,则子夏当名之为“拘谨派”?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