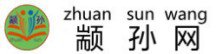颛孙师传(二十五)楚卫途中与隐者论道(2)
时间:2025-07-30 11:46 来源:zhuansun 作者:zhuansun 点击:次
“子张,” 孔子忽然开口,打破了夜的宁静,“你在想什么?” 颛孙师站起身,走到孔子面前,躬身行礼:“弟子在想,那隐者之言,是否有理?” 孔子放下竹简,抬头看着他,火光在他眼中跳动:“隐者避世,吾等入世,道不同而已。你且说说,你以为何为‘道’?” “弟子以为,道者,当以仁为核心,以礼为准则,行于天下,使百姓安居乐业。” 颛孙师答道,他曾多次听孔子论道,对这些基本理念早已烂熟于心。 “说得好,” 孔子颔首,“可如今天下大乱,诸侯征伐,大夫专权,仁礼不行,你说该如何?” “当如老师这般,周游列国,劝说诸侯行仁政,复周礼。” “若诸侯不听呢?” 孔子追问。 颛孙师一时语塞,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在他看来,只要道理正确,总有诸侯会听从。可现实却是,孔子周游多年,虽曾短暂在鲁国、卫国为官,却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 “老师,” 他迟疑地问道,“若无人听从,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?” 孔子站起身,走到帐篷外,望着夜空中的明月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只要吾辈坚守此志,总有一日,道可行于天下。” 他的声音不高,却充满了坚定的力量。 颛孙师站在孔子身后,望着那轮皎洁的明月,心中豁然开朗。他明白了,孔子的坚持,并非为了一时的成功,而是为了传承那份仁礼之道。即使身处乱世,也要坚守本心,这或许就是 “士不可不弘毅” 的真谛。 夜色渐深,营地渐渐安静下来,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,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。颛孙师躺在自己的铺盖上,却毫无睡意。他起身走到篝火旁,拿起一卷《诗》,借着微弱的火光翻阅。当看到 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 这句时,他不禁喃喃自语:“是啊,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吾辈虽处乱世,亦当以维新为己任。” “你这‘维新’二字,解得有意思。” 子路不知何时坐到了对面,手里拿着块烤熟的兽肉,“前年在鲁国,季康子想变法,你还骂他‘擅改祖制’呢。” 颛孙师放下竹简,接过子路递来的肉:“那时我以为,复周礼便是守旧。如今才明白,‘维新’不是变道,是就道中求新。就像这兽肉,烤法可变,肉的本味不能变。” “你这比方,倒比回子的《易》卦好懂。” 子路咧嘴笑起来,火光映着他脸上的刀疤,“我年轻时在乡野,见着农夫种稻,今年用井水灌,明年引山泉,法子总在变,可稻子还是要春种秋收。” “子路师兄这话说到了根上。” 子贡披着件外衣走来,手里还拿着个酒囊,“《诗》曰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’,道是本,法是末。去年在卫国,孔文子问政,夫子说‘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’,便是教他在守道中求变。” 颛孙师接过酒囊抿了一口,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,暖意从丹田升起:“我从前总想着,要像利剑一样劈开乱世。今日才知,真正的道,该像这江水,能穿石,也能绕滩。” “能明白这点,你这剑才算没白佩。” 子路拍着他的肩膀,力道大得让他差点坐不稳,“明日过了淮水,便有场硬仗要打。那边的山匪专抢游学的,听说前几日还劫了孟孙氏的车队。” “师兄要多加小心。” 颛孙师摸了摸剑柄,“我这几日悟了个道理,勇不是硬拼,是该出手时才出手。” 子贡在一旁笑道:“这就对了。明日见了山匪,先看我眼色,能智取便不动武。” 他晃了晃酒囊,“我这舌头,可比你们的剑管用。” 三人正说着,颜回抱着一卷书走来,见他们谈得热闹,便在旁边坐下。颛孙师见他眼下乌青,知道他又熬夜看书了,便把剩下的兽肉递过去:“回师兄,尝尝子路师兄的手艺。” 颜回接过肉,却先撕下一小块放在地上,口中念念有词。颛孙师知道他这是在祭天地,想起自己方才狼吞虎咽的样子,脸又红了。 “方才听你们说‘变通’,” 颜回慢慢咀嚼着肉,“《中庸》有云‘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去年在宋国,夫子被桓魋追杀,绕着大树躲避,便是变通;但始终不肯为桓魋效力,便是守道。” 他放下肉,拿起颛孙师的《诗》卷:“就像这句‘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’,‘旧邦’是本,‘维新’是用。你看这竹简,竹是本,编是用,缺一不可。” 颛孙师望着篝火中噼啪作响的竹枝,忽然想起孔子说的 “君子不器”。原来真正的君子,既要是坚实的竹,也要是柔韧的编,能方能圆,却始终是承载道义的竹简。 次日清晨,众人继续北行。离开了楚地,沿途的风光渐渐变得熟悉起来,道路两旁的田地里,已有农夫开始耕作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。颛孙师的心情也变得轻快起来,他不时与身边的弟子交谈,分享着自己昨晚的感悟。 行至正午,队伍来到一处山脚下的小村庄。村口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,树干粗壮,枝叶繁茂,投下一片浓密的树荫。孔子决定在此处歇息片刻,让弟子们补充些饮水和食物。 颛孙师随着众人来到银杏树下,刚坐下没多久,就看到一位老者拄着拐杖从村里走出。那老者须发皆白,面容清癯,眼神却炯炯有神。他径直走到孔子面前,拱手行礼:“先生可是孔丘?” 孔子连忙起身还礼:“正是在下。不知老丈有何指教?” 老者打量着孔子,又看了看周围的弟子们,缓缓说道:“吾闻先生周游列国,欲以仁礼匡扶天下。可如今诸侯争霸,民不聊生,仁礼又能奈之何?” 这一问,与昨日那位隐者的话语颇为相似,却更为尖锐。弟子们都屏住了呼吸,看向孔子,等待着他的回答。 孔子微微一笑:“老丈此言差矣。正是因为天下大乱,才更需要仁礼。譬如医者,正因有疾病,才需救治。若天下无病,医者何为?” 老者摇了摇头:“先生此言,吾不敢苟同。疾病尚可医治,乱世却难匡扶。昔日夏桀、商纣之时,亦有贤臣劝谏,然终未能挽回颓势。先生又何必白费力气?” “老丈可知,” 孔子的语气依旧平和,“商汤伐桀,武王伐纣,正是因为夏桀、商纣不行仁政。若无人坚守仁道,何来汤武革命?吾辈今日之行,虽未必能见成效,却可为后世埋下仁礼的种子。待时而发,便可燎原。” 老者正要开口,子路却忍不住上前一步:“老丈这话就错了!我年轻时在乡野,见着有人掉井里,难道因为井深就不救了?纵是救不上来,喊声救命也是该的!” 老者瞥了他一眼:“匹夫之勇,何足言哉?桀纣之时,比干强谏而死,微子去之,箕子为奴。三种选择,哪种更高明?” “自然是比干!” 子路梗着脖子,“宁死不失其节!” “不然。” 子贡摇着扇子走上前,“老丈问的是‘高明’,不是‘气节’。微子去之,保存了殷商的血脉;箕子为奴,传下了《洪范》九畴;比干死谏,只留了个忠臣名声。三者皆是行道,只是方式不同。” 他收起扇子,“就像这银杏树,根在土中是隐,叶在风中是显,皆是生机。”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赞许:“这位先生倒是通透。” 他转而看向一直沉默的颛孙师,“这位佩剑的后生,你以为呢?” 颛孙师深吸一口气,往前走了三步,既不像子路那样锋芒毕露,也不像子贡那样从容不迫:“弟子以为,三者皆是‘仁’。比干之死,是‘杀身成仁’;微子之去,是‘全身行道’;箕子为奴,是‘隐忍传道’。就像我手中之剑,可斩奸佞,可护典籍,可藏于鞘中静待时机。” 他拔出剑,剑身在阳光下泛着寒光:“关键不在剑如何用,在持剑人心中是否有‘仁’。” 老者抚着胡须笑了:“后生可畏。孔丘有此弟子,不枉周游一场。” 他转身向村里走去,走了几步又回头,“过了前面的芒砀山,便是卫国地界。那里的守将是弥子瑕,此人虽贤,却与灵公夫人南子交好,你们要当心。” 孔子对着老者的背影深深一揖:“多谢老丈指点。” 待老者走远,子路拍着颛孙师的肩膀大笑:“行啊子张,这番话比你在楚国朝堂上说的还中听!” 子贡摇着扇子:“就是剑拔得太急,吓了我一跳。” 颜回在一旁轻声道:“《诗》曰‘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’,你今日这一番话,可比昨日又精进了些。” 颛孙师收剑入鞘,耳尖发烫,却挺直了脊梁。他知道,自己离 “君子” 还有很远,但至少已明白,君子之道,不在虚名,在实处。 队伍继续前行,颛孙师的脚步变得更加坚定。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急于证明自己,而是开始用心观察身边的一切,体会孔子所言的 “仁” 与 “礼”。他看到路边有位妇人在哭泣,便上前询问,得知其丈夫被征召入伍,生死未卜,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分给了她。 “你这性子,倒是改了不少。” 子路走过来,见他正帮妇人挑水,“换作从前,怕是要拔剑去找那征兵的官理论。” “师兄说笑了。” 颛孙师放下水桶,“那妇人要的是粮食和水,不是一场打斗。” 他擦了擦汗,“就像昨日渡河,硬闯只会翻船,顺势而为才能上岸。” “能明白这个,你这剑才算真正佩对了地方。” 子路从行囊里拿出个布包,“这是我攒的几枚刀币,你给那妇人送去,让她做点小买卖糊口。” 颛孙师接过布包,沉甸甸的。他忽然想起子路虽常说自己 “安贫乐道”,却总把俸禄分给穷苦人,原来 “仁” 不在嘴上,在手上。 傍晚时分,队伍来到一处驿站。驿站的官吏认出了孔子,热情地招待了他们。晚饭后,孔子在驿站的庭院中讲学,弟子们围坐四周,认真聆听。 “今日遇到的那位隐者,” 孔子说道,“其言虽异于吾辈,却也有可取之处。他提醒吾等,行道需知时,不可盲目。” “老师,” 子路问道,“何为知时?” “知时者,明晓世事变迁之理,顺势而为,而非逆势而动。” 孔子答道,“譬如草木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皆循其时。吾辈行道,亦当如此,时而仕,时而隐,皆为行道计。” 颛孙师恍然大悟,他之前总以为,行道就必须入世为官,如今才明白,隐亦可为行道。关键在于是否坚守本心,是否以仁为念。 讲学结束后,弟子们各自回房休息。颛孙师却辗转难眠,他来到庭院中,望着天上的繁星,思绪万千。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,他曾是鲁国的一位武士,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。父亲临终前曾对他说:“吾儿当立志,不为良将,便为良士。” 那时他不明白何为良士,如今他懂了,良士 者,以仁为甲,以礼为盾,以天下为己任。 |
- 上一篇:颛孙师传(二十四)感谢楚国和楚地风云
- 下一篇:颛孙师传(二十六)卫国正名之辩